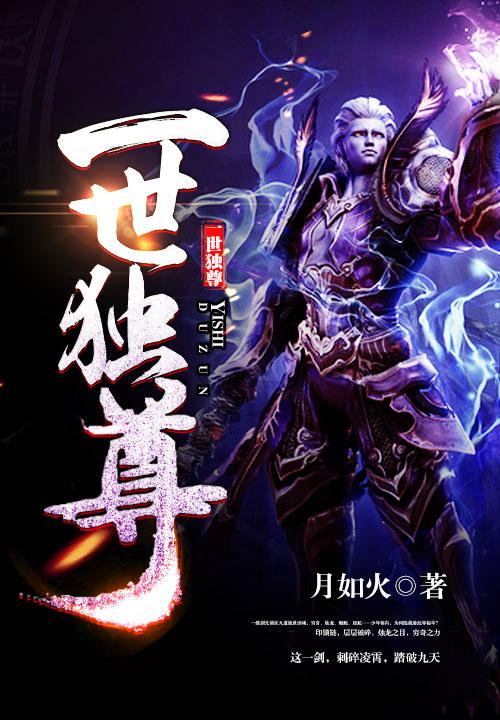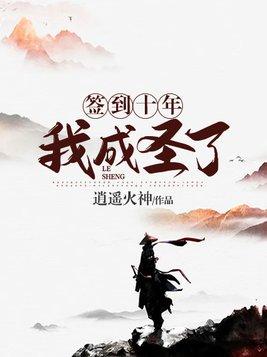书包书库>旧日音乐家 > 第五卷总结及请假(第1页)
第五卷总结及请假(第1页)
这一卷的字数写超了一大截,原本大纲估计的25W,结果直接飞到40W去了。
看来越往后期,在没真正动笔之前,是没法很好地估计收线所用的篇幅的。
所以完本的字数预期也得上调,从300W变成310-320W的样子,而且之后,估计还要更加注意篇幅的问题。
分享一个最新感受:稍微拥有一些写作经验后,我越来越意识到每卷、每章的写作字数并不是一个“任务”,而是一种“成本”(这里不是读者的付费成本,就是说的作者的写作成本)——每一次更新,我得拿着这固定每几千字的“燃料”或“子弹”,让剧情往预期的方向推进预期的距离,否则一旦拖沓叠加拖沓,整个大结构的把控就会变得非常难受,就如水会让燃料和子弹受潮一样。。。。。。
“新月”这一卷,其实,按照签约前最初的构思,这已经是最后一卷了。
对,这本书其实已经完结了,养书的别养了啊可以宰了(划掉)。
如果是都市文娱题材的一般大纲结构,主角一路推进,到最后一个数个世界最顶级的赛事上登顶,基本上就走完主线了。
剩下的话,再用个5-10章收拾一下,做点主角想做的事情,交代一下支线和次要人物的结果,再把情绪的余韵释放一下,让结尾定格在一个画面或一句台词中。。。。。。
完美。
不过现在的情况显然不是都市文娱小说,有好几个最初就设计好的大活还没开整。。。。。。
所以实际第五卷分割的节点,是在这个“原先文娱题材的收尾5-10章”之前,这个分割方式和之前的每一卷不太一样,以往卷与卷之间有一个大转场,所以尾声的情绪余韵释放更多,画面结束感强一些,而第五卷和下文是直接连着的,没有转场。
所以不排除有人可能觉得收得太快了,如果有这种感觉,那估计是分割点的变化导致的,不过没关系,还有下文呢。
当然,大家还是完全可以将第五卷结局视为一个《旧日音乐家》完结的IF线,如果这么去想的话,后续5-10章HE结局的收尾内容,根据上文提示自行脑补即可。。。。。。
然后还是按照惯例聊聊马勒的《升c小调第五交响曲》。
和书中类似,这部交响曲的创作时间,也是在世纪之交,工业浪潮下的1901-1902年,或人文思潮中那个延续性的名词,“世纪末”。
这段时间对于马勒的艺术生涯来说,是一个分水岭,因为,他人生中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,其中值得一提的,主要有三个方面。
第一个方面是反犹思潮。
与范宁在本卷的“登顶”结局类似,20世纪初,是马勒的指挥家与作曲家地位逐渐登上顶峰的时期。
但也是欧洲反犹主义情绪滋长最快的历史时刻。
虽然整个德语区域的反犹渊源是由来已久,但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,经20余年的进展,在奥匈帝国区域,这种思潮已经彻底变成了一场有组织有条理的政治运动。
“从1897年至1907年,虽然表面看来是马勒在事业上处于巅峰状态的十年,但正是在这十年里,马勒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作为一个犹太人的巨大压力。”
——克劳斯·费舍尔《德国反犹史》
所以第五卷中无处不在的管控氛围,其现实出处于什么,就无需再赘述了。
尤其是结尾庆典日的剧情上,为什么范宁会忽然想到“黑色贝九”,懂的人都懂。
第二个方面是实质意味上的死亡经历。
1901年年初,马勒患上了因肠道溃疡造成的出血症,按照他写给理查·施特劳斯的信件中的话来说,“是一场“致命的出血症”,我失去了2。5公升的血。”甚至还表示“我感觉我的时日不多了。”
当然,回过头看,经过一系列治疗,结果有惊无险(就像读者看小说也知道主角不会在半途噶了一样),但是这次鬼门关的经历绝对进一步加深了马勒对死亡叙事的阴影,康复之后他立刻回归原来的指挥岗位,也更感艺术使命的紧迫催促,加快了交响曲的创作。
这个鬼门关的现实经历,第五卷“范宁从失常区走了一趟再回归”的背景即是呼应,也对应当局约谈、游轮遇刺、波格莱里奇亲自带人等一系列实实在在的死亡威胁。
第三个方面是感情线。